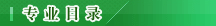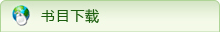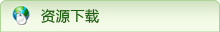|
南开大学历史系余新忠[1]博士的新着《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甫一出版就立刻广受大陆各界的赞扬,光从大陆学界有关此书的评介不断就可就看出这种研究取向的著作似乎是令人耳目一新。[2]本书修改自作者二○○○年的博士论文,洋洋洒洒四百多页,光是参考数据部分,原始史料就多达四百多笔,近人研究亦有两百多种,该博士论文更荣获大陆「二○○二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作者透过新的研究视野和新材料探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这样的研究趋向或许放在台湾或欧美的医疗史研究脉络下来看不算什么创举,但从大陆医学史一直位于历史学界中非主流的位置来看,本书无疑是大陆学界近年来的第一部重量级的「医疗社会史」专著。
在大陆的医史学界,以往有关疾病史的研究大多是探讨疾病本身,少有从疾病与社会的角度探讨的。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不仅是想从疾病医疗的角度勾勒中国近世独特的社会变迁脉络,其最终目标更希望能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特质。因此,本书在探讨清代江南瘟疫状况的基础上,特别关注以下的课题: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很明显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将焦点放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上,而且企图和以往研究明清社会史的学者对话,作者将瘟疫问题放在两个较大的学术脉络──「明清社会发展问题」和「明清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问题」上。全文共七章,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江南瘟疫的生态社会背景」、「江南的疫情」、「江南对瘟疫的认识」、「江南瘟疫的成因」、以及「江南瘟疫和社会之互动」。
作者在导论部分点出了历年来历史学界对疾病社会史研究的缺点,(1)仅对个别地区的某种疾病做研究,缺乏全面性的研究;(2)缺乏有关生态问题深入而细致的研究;(3)目前研究仅局限于国家与社会对疾病的响应,甚少对病人及病家心态的研究;(4)对疾病爆发流行的原因,未能做到结合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深入研究;(5)研究人员的医学与疾病学修养有待提高;(6)对白喉和疫喉痧等清代常见的疾病甚少研究;(7)数据运用上,医书和笔记文集的利用有限。从作者对疾病史的研究回顾看来,我们发现,作者对话的对象似乎仍局限在以往大陆的医史和历史学界,对于欧美盛行以久或台湾近年来新刊的疾病、医疗与社会的研究的掌握仍有待加强。
第二章说明江南虽拥有较其它地区优异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劳动力充足、便利交通、星罗棋布的市场网络、密集人口和频繁流动、具御灾能力的日常生活、普及的文化教育、好鬼尚巫之民间信仰),不过这些优势在构成江南繁荣富庶的促进因素和具体表征同时,也为致病微生物的滋生、肆虐提供了便利。
第三章主要是利用大量的江南方志制作出江南的疫情年表,进而分析江南的疫情。作者认为,江南瘟疫较密集地区分布在以苏州府、松江府与太仓州为中心的苏南和杭嘉湖平原上,其空间分布有两个特点:(1)瘟疫爆发次数的多寡基本上同社会发展的水平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说,以苏州、松江、太仓为中心,由东向西,由中向南北两端递减。(2)瘟疫发生多少与沿海与否有密切关系。在时间上,呈逐渐递升的态势,其中顺康时期较少发生,而咸丰以后增长较快,雍干和嘉道虽有增加,但增幅较小,发病季节多在夏秋两季。瘟疫的种类方面,除了各地普遍存在,早已成为地方病的天花、麻疹外,以霍乱、伤寒、痢疾和急性肠胃炎等肠胃道传染病为主(有关「地方病」的定义,见本文讨论部分)。从清中叶开始,白喉、猩红热等喉科传染病渐趋增多。至于真性霍乱在清代江南的历史虽不到一百年,但却是对当地社会影响最大的瘟疫。至于十八世纪以后开始流行的烂喉痧、白喉究竟是否如诸多学者所争论的是从境外移入的,作者在这并未坚持己见,只语带保留地说「不管这些疾病的病原是否新传入,它们出现大范围的流行则无疑在清代康熙以后……」。总体上,清代江南瘟疫所带来的破坏并未如当代一些初步的研究所认为的那么大,瘟疫对江南的社会影响可能更主要地体现在心态和风俗信仰等方面。
第四章「清代江南对瘟疫之认识」:作者结论有以下几点,(1)清人对瘟疫病原的认识基本上是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病两者长期并存。(2)清人在疫气致病基础上形成的对瘟疫流行因素、传染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已比较系统全面,但总体上,其理论基本没有突破「疫气传染」的认识框架。(3)有清一代对瘟疫的认识出现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是明清之际「戾气说」的提出和发展;二是清末西方病菌学说的传入和接受。(4)传统医学是一种关乎整体的系统生态医学,对外感染疾病病原的认识一直以「气」为基础,清代的「戾气说」推进了当时人对瘟疫的认识和医疗的发展。
第五章「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析」则说明清代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稠密的人口、以及卫生习惯等因素都非常有利温疫的流行。在众多疾病制约因素中,灾荒和战乱是瘟疫发生的必要诱因,而人口与瘟疫的流行有密切关系。究竟清代江南人口与瘟疫的变化有何关系?作者从人口成长与人口密度两方面来探讨:经作者推论,清代人口与瘟疫的变化在前期的相关性较高,乾隆末年以后渐趋下降,到了晚清,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引发争战,江南人口大幅减少,出现了反比关系,作者的解释是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人口与瘟疫的相关性较高,一旦外界干扰越大,其相关性就越低,甚至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会出现反比关系。至于兵荒马乱之际为何就会呈现反比关系?作者似乎并未做进一步解释。此外,作者发现在灾荒或其它外部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人口密度是决定当时某一地区是否会发生瘟疫的最关键因素(p.164-168)。
第六章「江南瘟疫和社会之互动」则是作者用力最深的部分,全书446页中,本章就占了160页,本章简单地说,主旨在探讨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第一节「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部分,作者从「趋避疫鬼」、「卫生」、「避疫、隔离和检疫」及「人工免疫」四部分着手。作者此节的重点放在种痘部分,其结论是人痘的施种,对清代人口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影响不大。第二节则透过实例说明江南各界对瘟疫的救疗措施。第三节「医学与瘟疫」部分则从「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资源的社会化」探讨江南瘟疫的流行与温病学派兴起的关系,以及医疗技术与知识普及化的问题。第四节则从瘟疫对人口和生态影响两部分来说明瘟疫对社会的影响,作者在此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在于,我们应该对于清代江南瘟疫带来人口的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换句话说,瘟疫显然没有对江南的人口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在结论部分,作者归纳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随着瘟疫的增多与环境的变化,当时人的预防、卫生观念和行为也有所进展。例如,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社会和官府合作共同保护环境的行动在江南地区应运而生。嘉道以后,由于水质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到了晚清,在西方思潮和制度的影响下,当时人还丰富与发展了「卫生」一词的含义。在人工免疫方面:不仅发明了人痘施种术,而且在牛痘传入后,其推广的普及率较欧洲还要来的高(p.345-346)。
清代江南活跃的社会力量、充裕的社会医疗资源不仅在疾病救疗方面弥补了国家的消极,而且较以往更具成效。乾隆中期,特别是嘉道以降,出现了日常性救疗设施(综合性善堂、医药局)逐渐增多的趋向,这些变化,除了在数量增加和同治以后专门的医药局突然激增外,更重要的是在内涵上有所改变,开始依靠稳定且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例如商行铺户的抽捐等(以往则主要是靠社会捐助或官员的捐廉,以及田产、房产的租金),并透过收取号金的方式以减少资金缺口,从纯粹的慈善机构逐转向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未必会直接导致现代医院的出现,但至少,在社会医疗资源上,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p. 346)。
此外,地方官府也开始较多参与日常性疫病救疗设施的开办。不论是种牛痘的引进还是西式医院的设立,都是透过地方精英和地方官来推广,之所以会被地方的社会力量所接受,究其原因则与人痘接种术和医疗资源的日趋发展等传统因素有关。可见,尽管现代卫生医疗体制可能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但其动力与运作的方式相当大的比例仍源自中国社会本身的特色,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将民间与非制度性的内容纳入官方制度化的形式中而已。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动并不完全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而是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运作;而且,它最后为清末国家相关制度与措施的改变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p. 348)。
(二)透过以上讨论,作者发现,若将人口和经济等因素不纳入考虑的话,则可看出清代江南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力量的活跃。这种活跃,不仅是指地方精英承担了地方上大量的工作,还因为它能对地方社会问题做出必要的反应,以弥补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制度缺失。但这是有弱点的,由于社会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不平衡,其活动多为自发和随意性质,以及本身不具有任何强制力。因此在疫病救疗、预防卫生观念和设施的推广等方面,其作用的发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甚至会影响到某些富有成效的疫病救疗观念和措施的推行。此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绅阶层,虽然对待技术一般都能采取开放的态度,但在价值取向上却较保守,这固然有利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但也阻碍了社会的转变,这使得整个社会缺乏长远的目光和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计划与措施(p. 348-349)。
(三)从以上江南地区的反应可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非但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的对立日趋严重的现象,反而在兴办医药局和牛痘局之类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密切合作的现象。此外,作者得到的结论是我们有必要从中国社会本身的发展脉络来理解明清社会力量不断活跃的历史意义。这个意义不在于社会力量借机促成民主和自由得到发展,而在于促发地方官员关注并举办一些缺乏制度规定,但实际需要的措施(p. 351)。
在清代江南,生态的改变对瘟疫的暴发和流行所引起的影响日趋明显,瘟疫已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经济行为所付出的生态成本中的重要项目之一。若和十九世纪前的欧洲相较,江南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相似的是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和疫病流行的日趋频繁,不同的则是江南的瘟疫一直未对人口造成结构性的破坏。在清代江南,瘟疫作为旧生态体系中保持人口资源间平衡的重要调节功能渐趋丧失,旧体系中的生态平衡也逐渐被打破,这些似乎都说明了它的社会生态已经开始脱离了旧有的生态体系(p. 352-354)。在此,余新忠企图引用西方的研究来论证其研究成果的特殊性,其精神值得鼓励,但必须注意拿来比较的是什么数据?从他在页353注(一)所引的参考数据来看,他参考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劳岱(Fernand Braudel)的研究(《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事实上,布劳岱的研究距离现今已有一段时间,这之间应有许多更具代表性的研究可以援引,例如已故的英国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的作品。
笔者曾经做过明清痲疯病的研究,深知研究疾病史的困难度,对于余新忠博士的能在短短时间内做出这样的成绩深感佩服。以下仅就笔者阅读过程中,所碰到的一些疑问,就教于本书作者:
(一)作者在许多地方所根据的资料都太过薄弱,但却作出大胆的推测,例如页83-84推测天花的流行具有不规则的周期性。作者主要的根据是方志里的材料,他找出清代江南有明确记载的痘疫有现次10县次,其中7县次在宁波府,即截取乾隆五十年至嘉庆十一年的22年间,慈溪和象山县分别有两次痘疫记载,作者假设乾隆五十九年的「象山大疫」为痘疫,这样三次的间隔就是9年和12年,因而推论这「反映了某种不规则的周期性」。透过区区这几则数据所统计的数字而做出的「不规则周期性」推论,我们觉得值得商榷。首先,方志中所谓的「痘疫」就是指天花吗?其次,只有三个年份的数据就要说当时天花的流行有「不规则的周期性」,这样的推论只能说是推测罢了,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可言。作者甚至以此推论,进而在页246论证当时种人痘的无效:「大约每隔十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一次大范围的天花流行。这表明,当时的种痘并没有对天花这一疫病的流行模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它可能在上层社会会有较高的接种率」。页344,作者在结论说道:喉痧和白喉大规模地发生在十九世纪以后苏州、上海等大城市,「这显然与当时环境日趋变坏和空气质量恶化有关」,有关这点推论,我们并不反对疾病的发生与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但关于烂喉痧和白喉究竟与工业发展的关系如何?作者其实没有举出太多的实例说明这项论点,作者只举出两则较具体的例子,一则是乾隆二年(1737)苏州染坊污染水源的例子,另外一则是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的嘉定「晨降微雪,色黑,按之即消,黑雪的出现,当是上海严重工业废气污染的结果」。事实上,作者所举的苏州染坊污染水源的问题,并不能用以解释十九世纪苏州等大城市流行烂喉痧和白喉的原因,因为根据苏州碑刻史料记载该事件之后,官府已规定苏州阊门附近聚集的染坊都要搬离到娄门,之后再也未见到染坊污染的问题。此外,这里还存有两个问题,一是究竟当时工业污染到底严重到程度,是否有到作者所说空气质量变坏的程度?一是工业污染与疾病究竟有何必然关系?当前一项的相关研究都不充足时,就大胆推论第二项,我们认为应当持保留看法,更何况作者自己都说道:「当时的环境污染更主要还是由生活垃圾不能得到适当的处理造成的」(页173),可见作者自己都说道当时的污染还是以家庭污染有关,这似乎有点前后说法不一致。
(二)余新忠深信「通过深入发掘数据和综合利用多种方法与数据,对某次瘟疫的疫死人口数与疫死率做出一概略性估算是有可能的,而且有助于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故就此而言,将瘟疫因子引入人口史研究是件值得高度评价的工作。」[3]因此,他透过清代八个不同时空的的瘟疫个案,来探讨瘟疫对江南人口的总体影响。很明显地,他对大陆人口史学者曹树基和李玉尚的鼠疫和霍乱研究颇有微词,他认为他们俩高估了瘟疫所带来的四成致死率,余新忠则认为在和平时代,一般性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率顶多2%以下,较严重的可达到2%-3%;至于像霍乱的致死率虽在小小区中可高达到15%,但一般很难超过5%,战争期间有可能高一点,但不会过20%。至于双方的推断的数字差距为何那么大?余新忠认为这因为「李玉尚的立场多少带有一定的 “批判”倾向,往往立足于现代的眼光和标准来认识和批判历史行为。」[4]究竟谁的说法较正确,笔者不敢断言,但我觉得这些数字反映的意义似乎不大,因为这些资料的限制似乎不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方法或问题意识有所不同就能解决的,要精确地统计出疾病的致死率的前提是要有详细的调查数据,而非单凭几个个案和方志中模糊的人口数概念就可推算出来的。
(三)作者在书中许多地方所说的「地方病」概念与我们一般常用的看法不同。例如页82说道:「清代江南的瘟除了各地普遍存在,早已成为地方病的天花、麻疹外,以霍乱、伤寒、细菌性痢疾和急性肠胃炎等肠道传染病为主,从清中叶开始,白喉、猩红热等喉科传染病渐趋增多,疟疾仍为各地夏秋不时出现的地方病」。这段话的问题在于天花和麻疹不只在清代江南一带出现,为何还会被称为「地方病」,笔者百思不解,难不成海峡两岸对「地方病」的认知有所不同吗?当代大陆学界对地方病的定义很明确地指出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特殊疾病:「发生在某一特定地区,同一定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的疾病……此外,地方病多发生在经济不发达,同外地物资交流少以及卫生条件不佳的地区(例如流行在中国黑龙江地区的克山病)」[5],可见余新忠的地方病概念与大陆学界的看法不同。其实,早期医史学家谢利恒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就对地方病有以下定义:「地方病者,限于一方水土之病,而有一方治疗之法,不尽通行于各地也。」[6]此外,近来一些医学史研究者萧璠、玛塔.韩崧(Marta Hanson)和梁其姿的相关研究对地方病或风土病的诠释也与余新忠的概念明显不同。[7]
(四)作者在谈到瘟疫的种类时,举了五个原因说明要准确的判定历史上所发生的疾病为现代医学所称谓的何种疾病,有其危险性。但其实他又不时的想说明古代的疾病究竟是现代医学定义下的何种疾病,例如页102说雍正十一年苏松地区的大疫很可能就是「伤寒」,我们从上下文中丝毫看不出这项解释的根据;页103提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嘉定一带红痧症的流行,作者从丁甘仁所辑《喉痧症治概要》中所描绘症状「发于夏秋、呕恶、舌苔白腻、外热极重而里热不盛」推论,应该有可能是伤寒;页115说道;「根据汪的说法,大头瘟乃因以伤寒法误治肿腮而形成,实为一种疾病。由此似乎可以明确,这四种病实为一种疾病,基本相当于现代的流行性腮腺炎。」文中指的四种病是大头瘟、虾蟆瘟、捻头瘟、羊毛瘟,作者不仅将这四种瘟病归为是「流行性腮腺炎」,还进一步推论大头瘟若是流行性腮腺炎该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极有可能是现代的「脑膜炎」;而虾蟆瘟的症状可能是范行准所说的「猩红热」;页117则提到羊毛瘟与现代医学中的「带状疱疹」似有相似之处。页317引用《历年记》的瘟疫记载时提到:「具体为何种疾病,并不明确,不过从感染率如此之高这一情况来看,仍是菌痢的可能性较大。」这些古代病名的推论大多建立在这些疾病的病征与现代医学定义下的某些疾病病征有相似之处,病征相似就是同类型疾病吗?这与作者一开头的呼吁似乎有点背道而驰。
(五)页152-154中有一小节「晚清西方细菌学说的传入」,作者只花了不到两页的篇幅简单的交代了西方医学中的细菌理论在1900年前开始传入中国后,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医学。这样的说法其实过于简化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经过。作者甚至在结论方面提到对瘟疫的认识在清代有两次重大的发展,一次是明清之际的「戾气说」的提出和发展,一次是清末西方病菌学说的传入和为人所接受。事实上西方医学传入近代中国的过程似乎并非像作者所说那么平顺,中国医家亦非全盘的照单全收,其实这之间是有许多的「冲突」和「妥协」的互动过程,关于这点,布莱蒂.安祖(Bridie J. Andrews)的肺痨与近代中国细菌理论的传入的论文有详细的探讨;[8]此外李尚仁近年来的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研究也处理过相关课题。[9]
(六)页122作者引用徐晓望与刘枝万的研究说道:「在当时,五圣、五显、五通、五圣,名虽异而实则同。在瘟神信仰中,五瘟、五通、五圣等,属于五帝系列,可能是天廷之瘟部正神,司掌时疫。」其实,这样的说法似乎忽略了「五通」信仰自唐宋以来在历史间转变的复杂性,近来已有许多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值得作者参考,例如康豹(Paul R. Katz)在《台湾的王爷信仰》中说道:「另外有三种不同的神明——五圣、五显及五通,虽然也以五为单位,但是与五瘟使者、五瘟皇扯不上关系。因为这三种神明的称号有时会重迭,将上信徒的误解,因此使不少明清以来的学者认为祂们名虽异而实同。其实,五通原是一种妖怪,尤其是猴精;五圣为元末明初阵亡之厉鬼;五显原是徽州的一种英灵信仰。」[10]此外,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与麦可.斯隆伊(Michael Szonyi)的研究亦探讨了这几个名称的形象的转化过程。[11]页236谈到清代对天花的治疗时,认为国家和官府甚少作为,即使有,也「几乎完全是针对皇族和喀尔喀诸藩的」。有关这个课题的研究,台湾学者张嘉凤的博士论文和单篇论文已有最新的研究成果[12],可惜作者只引用了早期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953)和廖育群的《歧黄医道》(1991)的看法。
(七)作者在第六章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在介绍人痘和牛痘在江南的引进和推广,似乎让我们感觉到清代医家和地方精英相当重视天花这疾病,但作者又在许说地方说天花较其它疾病如霍乱和白喉的影响要来的小,笔者疑惑的是为何影响那么小的疾病,反而会受到较多医家的关注呢?
(八)页310作者指出明中期以后的文献中,常出现对庸医杀人的指责,余认为马伯英对此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民间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差而致」,进而批评马这种说法是以今度古而得出的结论。关于这点,笔者觉得这是余新忠的误读,事实上,马伯英所谈的只是泛论,并未只针对明清时期,而余新忠谈的却是明中叶以后医学发展现象,若以此批评马伯英的结论,来凸显「正是当时医学知识的日趋普及和医生职业渐趋开放所造成的」现象,这样的批评似乎有欠公允。
(九)页296田雪帆《时行霍乱指迷辨正》一书引文有误,「世俗所称吊脚痧一症,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阳肝经」应改为「阴肝经」,「轻者两三剂(一日中须进二三剂)」应改为「轻者两三剂(一日中倾频进二三剂)」;「其神方也」应改为「真神方也」。页298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引文句读有误,似乎应改为:「……未交芒种,薄游海上,……故伏邪不能因生发之令,外泄以为温,……毫无觉察。」。页420误将笔者姓名误植为「蒋竹三」。
上述笔者的一些疑惑和评论丝毫不减本书对疾病史研究的贡献,余新忠先生的专著不仅为大陆的医疗史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其书中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也让我们重新去省思「疾病史究竟该怎么研究?」关于这点,余新忠在〈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一文中有进一步阐释,该文相当犀利地观察到当前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尚需要加强的地方,例如医疗资源、民间疗法、家庭在医疗中的地位及其变迁、医学与医家的地位、医病关系等等。
对于这些意见,我们深表赞同,但是除了上述课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之外,我们认为在研究取向上亦应该有所突破,例如该如何跳出传统社会史的问题意识框架,尝试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疾病史。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查理士.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的名著《形塑疾病:文化史的研究》(Framing Disease: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颇值得我们参考,他在书中检讨了过去西方医学史界以「社会建构论」来研究疾病史的缺点,这些研究常忽略了(1)疾病概念形塑的过程(Framing Disease);(2)疾病概念形成后,如何影响医疗政策、日常生活以及医疗活动(Disease as Frame, Negotiating Disease, Disease as Social Diagnosis )[13]。以文化史角度来研究疾病史,这在西方学界行之有年,反观中国史方面,近来才渐渐有一些学者采取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例如前面提到的布莱蒂.安祖(Bridie J. Andrews)的「肺痨」研究、夏互辉(Hugh Shapiro)的民国时期的「遗经」研究,[14]陆斯.罗佳斯奇(Ruth Rogaski)的满洲国的疾病与谣言的研究、[15]和陈秀芬的近代中国以前的癫狂研究。[16]这些学者中,又以夏互辉的文化史走向最为明显,〈遗经〉一文不仅追溯了医学思想的内在发展,更企图解释许多至今仍存在于东亚各国的独特文化——「肾亏」和「补肾」的文化。尽管上述这些医疗文化史的研究尚在起步,但其新的研究取向和成果或许能为我们日后欲探讨瘟疫与社会的课题时,提供不同的思考面向。
附录:余新忠近三年医疗史著作目录
(1)〈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6。
(2)〈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2。
(3)〈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2。
(4)〈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
(5)〈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2。
(6)〈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
(7)〈打通医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他山之石——评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医学史》〉,《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10)。
(8)〈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5。
(9)〈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10。
(10)〈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略〉,载《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年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1)〈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4
*大汉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讲师
[1] 余新忠大概是大陆近年来医疗史产量最丰富的研究者,光是从2001年至今,相关论文就有十一篇,参见附录。这些文章大多是从博士论文抽离出来发表的单篇论文(唯一一篇与博士论文较无关联的是回顾性论文〈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4: 158-168)。
[2] 这方面的书评性质大多是介绍性的为主,尚未见深度书评,大多是对此书称誉有加,我们可以举其论文口试委员王思治为代表,他的评价是:「“疾病医疗社会史”是一个前人涉猎较少的领域,近年来虽然有少数学者关注于此,但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创新。博士余君,选题既富开创性,论述尤其精详,读来引人入胜。」
[3] 〈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页162。
[4] 同上,页163。
[5]参见网站http://www.xyg-hb.com/huanjing/028.htm。
[6]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进学书局,1970),页59。
[7]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3.1(1993): 67-171;Marta Hanson, “Inventing a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From Universal Canon to Local Medical Knowledge in South China, the Seven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1997);梁其姿,〈疾病与方土之间──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性别与医疗》,页165-21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8]Bridie J. Andrews, “Tuberculosis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Germ Theory in China, 1895-1937,”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2.1(1997): 114-157.
[9]李尚仁,〈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学界对中国痲疯病情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4.3(2003): 445-506.
[10]康豹(Paul R. Katz),《台湾的王爷信仰》(台北:商鼎文化,1997),页28。
[11] Richard Von Glahn, “The Enchantment of Wealth: The God Wutong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Jiangn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2(1991): 651-714; Michael Szonyi, “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1997): 113-135.笔者也曾着有五通神与清代江南社会的关系的论文,〈汤斌禁毁五通神——清初政治精英打击通俗文化的个案〉,《新史学》6.2(1995): 67-112。
[12]作者只在导论部份研究回顾时提到张嘉凤的研究而已。Chia-Feng Chang, “Aspectss of Smallpox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6);张嘉凤,〈清康熙皇帝采用人痘法的时间与原因试探〉,《中华医史杂志》26.1(1996): 30-32;张嘉凤,〈清初的避痘与查痘制度〉,《汉学研究》14.1(1996): 135-156。
[13]Charles Rosenberg, Framing Disease: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此外还有Sander Gilman, Disease and Representation: Images of Illness from Madness to AID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 Hugh Shapiro的遗经研究诠释了为何在新旧典范互相冲击的民国时期,「遗经」会成为一般大众共通关注的焦点,见“The Puzzle of Spermatorrhea in Republican China,” i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6.3(1998): 551-596. 最近他又发表了十九世纪中国有关「神经」概念的诠释的研究,见“Interpreting the Idea of Nerv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之First Meeting of the Asi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Asia, 2003/11)。
[15] Ruth Rogaski, “Japanese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in Manchuria: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Meaning of Rumor, ”(发表于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举办之「明清至近代汉人社会的卫生观念组织与实践」工作坊,20003/9).
[16]陈秀芬(Hsiu-fen Chen), “Medicine,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Madness in Imperial China ,” (PH. D thesi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2003).
|